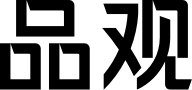擅长做经济史研究的64岁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教授Geoffrey Jones平生一共写了41本书,其中一本《美丽战争》传播甚广,这是一部化妆品商业史,从香水工业在法国的发轫一直讲到2010年美妆集团的全球版图。不过Jones觉得这本书有一处没说完的地方:韩国化妆品公司。
在这本302页的书里,正文部分提到“韩国”的次数只有5次,而提到如今韩国最大的化妆品公司“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只有1次。在2010年,他还没有太多写作素材。如今,他会用同事Pankaj Ghemawat写的《爱茉莉太平洋:从本土到全球化》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韩国化妆品公司不再是一个他能绕得过去的话题。
的确,韩国化妆品越来越有存在感了。根据欧瑞咨询公布的数据,2015年,韩国的化妆品产业价值为116亿美元,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31亿美元。韩国化妆品在中国风靡,以至于韩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了中国第二大化妆品进口国。
不仅如此,过去两年,欧美的化妆品公司的并购频繁和韩国化妆品发生关系。先是2015年,Estée Lauder并购将BB霜带入市场的品牌Have & BE.CO。紧接着今年7月 ,LVMH集团首次投资了韩国化妆品品牌,用5000万美元投资了估值7亿美元Clio Cosmetics。同月,Goldman Sachs和Bain Capital Private Equity也买了有近1000种产品的韩国化妆品公司Carver Korea的股份。
它们的生意并不是卖卖护肤品和口红那么简单。只要说出“韩妆”二字,大多数熟悉美妆的女生都能在脑海里想象与之对应的形象,而这种美学在英语里已生成了一个新的合成词K-beauty。
Geoffrey Jones在他的书中曾提到一个例子:为了把自己和巴黎这样的美容之都扯上关系,日本最大美容品公司资生堂把旗下高端护肤品系列直接用法文命名:Clé de Peau Beauté。同样的情况你倒是也能在如今的中国看到:一些中国化妆品公司在努力和韩国(而不只是巴黎和纽约)扯上关系,比如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韩束”和“韩后”,并花大价钱聘请韩国明星作代言人。

全智贤最新的电视剧《蓝色海洋的传说》又把HERA的147号色唇膏变成话题

《太阳的后裔》宋慧乔正在使用兰芝双色唇膏
美妆行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以往,美妆产品只是由部分大公司垄断, 主要在百货公司或者化妆品专门店(如丝芙兰)里销售。为了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品牌往往要花费巨额的广告费用,和电视、户外和时尚杂志的美妆版面合作,告知最新的产品信息和流行趋势。
然而如今美妆产品的信息传播渠道已经彻底民主化。与其相信时尚杂志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家的推荐,很多人都从社交网络里的“达人”身上获取经验,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各色口红试色、化妆步骤示范视频以及类似于“好用不贵的神器推荐”这样的文章,甫一发出便会迅速传播。
另一个主流渠道则是娱乐产品。2016年,《太阳的后裔》宋慧乔捧红了兰芝双色唇膏;《Doctors》女主角朴信惠代言的Mamonde唇釉、渐层打亮饼,还有李圣经的兰芝超放电丝绒双色唇膏也变成了互联网上的新鲜话题;《W-两个世界》韩孝珠则让她代言的秀丽韩进入大众的视野。
所有这些信息渠道的变化都催促消费者尽快购买并体验新商品。百货公司的推广角色让位于电商。消费者心态变得越来越娱乐化——她们不仅仅需要美,还需要因为新鲜带来的刺激和愉悦。
“每个月韩国化妆品牌都会提供一些新的东西。我的工作就是搞清楚哪一种新款能成为一时半会的新潮流,或者是真的成为化妆品界的新趋势。”生活方式类网站Refinery29的美妆撰稿人Joyce Kong说。
在制造新鲜感这件事上,没有人比韩国人做得更尽心尽力了。从2013年到现在,BB霜、CC霜、三色唇膏、隐形腮红、海绵眉笔、气垫腮红等诸多产品逐渐占领时髦女生的化妆台。裸妆、咬唇妆、Two-tone唇妝、韩式一字眉、无暇韩国美肌、果汁唇、“2/3妆”、韩式半永久定妆、宿醉妆,还有卧蚕妆——这些新鲜词汇层出不穷,以至于总有一些人在跟另一些人尝试解释它们的具体含义,有时候听众的表情就好像是在聆听最尖端科技术语或者是某一类古生物化石名词。
它们绝大多数价格平易近人,哪怕消费者买了不喜欢也并不可惜。这样一来,韩国市场的消费者没有什么品牌忠诚度。“这跟西方市场不一样。一般在西方市场,我们创造一种产品来解决一种问题。但在韩国,消费者并不把一个产品当成一个问题的答案,而只是许多化妆品的一部分。”化妆品包装公司Yonwoo International/PKG的市场总监Curt Altmann说。
的确,和韩妆让人眼花缭乱的招式相比,欧美化妆品显得有些正襟危坐了——虽然它们质量往往更高,但出新的速度则要慢上很多,也没有这么年轻花哨的名词来帮助推广。
美妆业素来需要噱头,而韩妆似乎把这个技巧玩到了极致。套用一个滥俗的说法——如果把整个韩国美妆界都视为一个公司的话,它完全符合“互联网思维”的定义:以量取胜,迅速测试市场,迅速调整产品结构。 其生存的秘诀在于不断研发新产品,紧跟消费者心态变化,甚至引领她们的消费意识。


咬唇妆之后,流行的水果妆


韩国明星在推荐欧美的化妆品,她们最近又捧红了阿玛尼的口红


韩国女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一种黄色小物,是Clarins最新推出的修护唇油
这样的模式,业界从快时尚那里借用了类似的说法,称之为“快美妆”。
“在韩国,化妆品如果产品有三年生命周期就算很长的了。化妆品生产商总是通过在原料、配方、应用的创新上来细分市场。”Curt Altmann说。他认为,化妆品牌的活力,一个关键的来源是创新能力,你更新得越快,就越容易吸引人,再加上相应的营销手段,从而带来相应的销售回报。
韩国化妆品生产商产品的研发周期现可缩短至4个月,而大多数美妆品牌的研发通常需要1年以上。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董事长徐庆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曾表示,流行趋势的变化是非常快的,韩妆的优势在于能不断地适应这种变化。
以该集团集团旗下的品牌的Innisfree为例,截止目前该品牌共推出了800多款新品,其中约有一半将在一年后将被淘汰。每年平均能推出200多款新品,差不多两天能推出一款的新品,但其中一半的产品第二年将不再销售。
基本上这就是你能经常看到韩国化妆品又推出新鲜玩意儿的主要原因。它们的产品不一定要在市场上存活很久,你能看到的爆款都是万里挑一之后的幸运儿。
“韩国化妆品公司的重点是创造趋势,产品推出得很快,然后迅速卖出去,然后又转入了下一个趋势。”欧睿信息咨询的化妆品和私人护理产品研究员Sunny Um告诉《好奇心日报》,“如今的消费者都已经被教育过,也知道很多化妆品的事,她们明白市场上的产品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她们来说,唯一的刺激就是市场上有什么新东西。”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和韩国化妆品公司背后统一而强大的代工厂体系有关。
代工厂在化妆品领域并不特别,它们也不只是服务于韩国化妆品品牌。1993年,欧莱雅刚进入韩国市场时,它的大部分产品靠进口进入韩国市场,很小的部分产品靠韩国当地的OEM厂来生产,以此占到了韩国化妆品市场4%—5%的份额。但韩国市场的这些OEM厂逐渐演变成了ODM厂 (原始设计制造商)。与前者接单生产的代工模式不同,ODM厂摆脱了贴牌的生存状况,它们向化妆品公司输出技术,引领韩国化妆品市场的研发。
在韩国市场,一家叫科丝美诗的公司和一家叫科玛的公司基本上平分了韩国的代工市场。
其中,不仅卡姿兰、韩粉世家、雅丽洁等品牌的气垫霜产品均由最大的代工生产商科丝美诗生产;像兰蔻、植村秀这样的大品牌的产品,也会委托科丝美诗在其韩国工厂代工生产。至于韩国最大的两家化妆品公司是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和LG Household & Health Care,它们自己持有高级化妆品的生产主动权,但它们部分的开架品牌也会交给韩国的代工厂。
以“谜尚”和“菲诗小铺”为例,这两个专注产品的推广和销售,把生产环节外包,大部分产品由科玛和科丝美诗生产。韩国化妆品企业Todacosa 2015年针对16岁至25岁女性推出品牌 “Too Cool for School”,为了降低成本,没有专设工厂,生产全部外包,其中40%的护肤产品出自科玛。
“ODM是这个行业很安静的角色。L’Oreal这样的公司基本上靠ODM。这说明,整个化妆品行业都不是产品研发有关,是跟品牌做市场的能力有关。” Geoffrey Jones告诉《好奇心日报》。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韩妆市场的最新趋势总是能迅速总一个品牌流入到另一个品牌。它们虽然都是不同品牌,包装也各有特色,但产品的特性总是非常相似;与此同时,不同的营销包装又可以保证它们互不侵权。现在,在韩国国内共有1800—2000个化妆品品牌。这还可能是最后在旺盛的国内市场竞争之后的留下的品牌数量。事实上,大部分的化妆品都出自同样几家代工厂。
打算明年进入中国市场的韩国化妆品品牌OOZOO是一个毫不掩饰自己代工厂背景的新品牌。5 月在上海参加美妆博览会时主推了它的明星产品,名为“Two Touch”结构的针剂安瓶面膜“OOZOO FACE MASK”。这款面膜将精华液分开储存待使用时才注入混合,据说这样可以“让有效成分发挥最大功效”。简单说来,这是一款带有DIY玩耍性质的面膜,再加上针管等“好玩”道具,它看起来很有新意。
在 OOZOO 的淘宝代购页面上,它的广告写着:“制作团队是丽得姿原班人马,生产工厂是雪花秀代加工工厂。”


Clio推出了新品The Kill Cover Stamping Foundation,粉饼是印章形状

韩国品牌Nakeup Face推出的眉笔,号称8天不脱妆

Innisfree的My Cushion DIY气垫BB霜


韩国品牌B&Soap推出的名为Coloring Paint Pack的面膜,长得像颜料,分别有补水、再生、清洁的功能



3CE推出的Mood Recipe彩妆系列,全是大地色


今年兰芝革新了它的爆款气垫BB,新颖之处在于粉芯用了3D格菱纹
曾经在欧莱雅中国的市场部做产品经理的马修对化妆品代工厂的事很熟悉。在他从欧莱雅离职后,他成为了他口中的“皮肤结构专家”。他做了一个公众号聊化妆品,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开发化妆品新品牌。
前两年在酵素很流行时,马修就接到一个韩国OEM厂的共享信息,他临时组成了一个团队开发了一个身体护理系列,特色产品是手部护理。马修用“权力变大了”来形容这种从跨国公司产品经理到自由职业者的角色转变。“这项工作在大的化妆品公司里面,很多部门的人分部门去完成了。突然都放在一起了之后,你的决断要变快,也需要很多创意和想法。”马修告诉《好奇心日报》。
过去5年,马修做成功的品牌有4个,都用上他积累到的化妆品产业链上的资源。要做出一个产品,马修要负责选化妆品的包材,想好品牌要讲的故事,找OEM厂来生产,决定最后的产品代理商,最后打包卖给雇主(由于协议的原因,马修不愿意透露雇主的名字)。
一般完成一个品牌的开发是2—3年,而以马修的经验来说,这其中最花时间的还是化妆品包材的开发。比如一个品牌需要新开发一个眼影盒,计划定位一个五色眼影盒,后来的开发步骤还包括确定眼影盒大概是一个什么形状,设计,找工厂开模打样,然后再大规模生产。这个包装的开发一般会消耗一年的时间。
根据他的描述,就算是新的小牌子,“中国化妆品还是和韩国的不太一样”。“我亲自陪过几个本土品牌和COSMAX做过沟通。中国的管理者们,觉得自己的品牌应该有自己的样子,哪怕多花钱开模,都希望是自己的产品不一样。”马修说。
这种生产思路自然会加快整个产品线的生产节奏。而品牌要做的事情就是快速测试这些产品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不行,又应该如何调整。
比如,Innisfree和伊蒂之屋在产品上架方面中国与韩国完全同步。其销售团队固定每月从每家门店的销售人员处获取消费者购买及选购行为的信息,再根据这些信息形成分析报告,作出相应的产品和门店架构调整——整个过程,其实和Zara这样的快时尚没有差别。
只不过,美妆产品理论上的生产时间要比服装周期更长。种类数量的庞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迭代的迫切。也正因为产品种类远多于普通品牌,Innisfree这样的开架品牌会选择专门开设店铺。
这个2004年第一次来中国,当时它和所有化妆品一样挤在百货专柜的品牌,两年后就全部撤柜了。等到2012年重回中国时,Innisfree降低了价格,并且把在韩国市场很吃得开的单品牌店模式带到了中国。
一般的化妆品品牌顶多只有300个SKU,看起来袖珍的百货商场和商超渠道就已经很合适了,而Innisfree却拥有800多个SKU,街边上或者购物中心的百平方米的品牌专卖店才能把它的全貌展现出来。
通常,店门口会立着一张因出演《继承者》在中国走红的长腿大哥李敏镐真人一样大小的照片,吸引那些对认识李敏镐,也对韩国明星有感觉的消费者。因为总是有新品,你还时不时能在网站读到信息:Innisfree推出了圣诞限量系列;Innisfree推出DIY气垫粉底,有100款粉盒可以选择;美妆博主Winnieee写的,“我买了Innisfree Cream Tint Lipstick,上色持久!强调是非常持久!持久的程度太夸张”;或者是少女时代的林允儿代言的Innisfree气垫BB后,跑去韩国杂志《Highcut》上了走穴,生活方式网站POPBEE再找她做一个“以封面的造型为蓝本,教大家如何运用3种化妆品,打造一个与允儿一样充满质感的清雅妆容。”当然,这个教程中的所有化妆品都来自innisfree。

欧美品牌正在试图追随这样的风潮。11月11日,Dior在纽约开了第一家化妆品精品店,这家店只售卖Dior的彩妆、香水等产品,没有成衣和皮具。就在同一天,Estée Lauder也在英国伦敦卡纳比街的SOHO开了它在这个市场的第一家独立门店。这家面积有700平方英尺的店将主推它为喜欢自拍的千禧一代开发的Estée Edit系列,但也会放一些雅诗兰黛的其他产品。
虽然,Dior和Estée Lauder都分别表示,它们会在这两家单品牌店里摆放一些有数字化特色的装置,比如让消费者拍个大头贴就可以自动换妆容,但事实是,它们可能不像Innisfree那样,能做到如此迅速的迭代。纵然开设了化妆品专卖店,也没有办法靠上新让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门。
可以说,韩妆和互联网是互相成就的一对:是消费者对于美妆产品的娱乐态度催生了如此朝夕变化的机制,而这个机制本身又推动消费者进一步求新求快,永远在追逐下一个潮流。至于整个行业是否会被裹挟着进入一个快速奔跑的阶段,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可能性极大。
“我用这本书来研究全球化,研究公司如何影响我们思考和认识美(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Geoffrey Jones在接受《好奇心日报》的采访时说。这句话套用到时下的韩国化妆品行业身上,或许再恰当不过了。
来源:好奇心日报
作者:张田小